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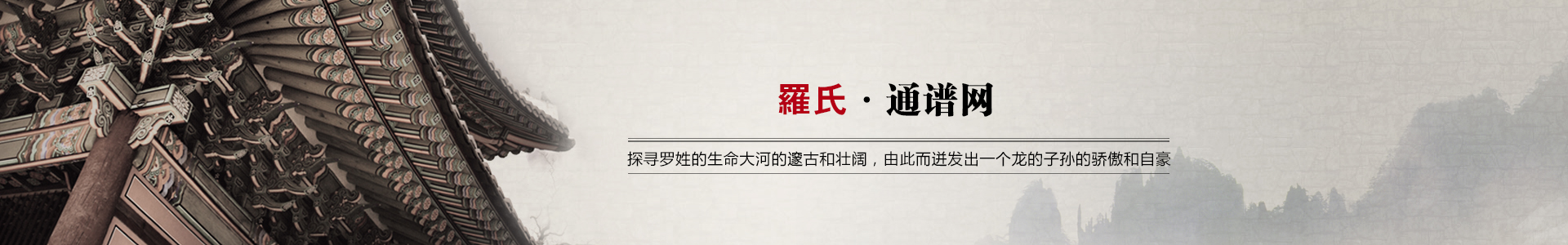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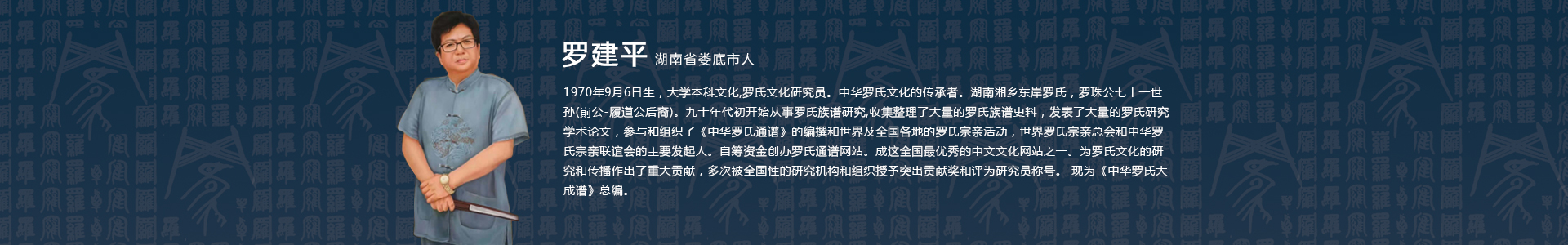
对《那地州官族罗氏宗谱》的看法
罗起君 发布时间:2006-11-30
1. 在广西生活的人都知道,广西壮族的构成成分不是纯粹的一种。对于壮族,大家都有所了解,但又不甚了解,包括《考辩》者。仰求于日本人来给广西壮族下结论,能说了解吗?纵观《考辩》的前言,不是依据历史上个别人的议论、个别事情,就是取证于个人的诗句,把有关壮族生活习俗套在一切之上,把中近古以往的广西人全部土著化、壮族化,否定移民的存在。甚至指责旧省志、旧县志,以及新著的广西《壮族通史》关于壮族的历史记载与研究。《考辩》为什么如此着急?当下修谱、续谱的支系越来越多,一寻根,不知不觉挂到中原一方,《考辩》担忧了:“而且如此一来,壮族作为一个渊源有自的独立民族群体还有存在的依据吗?”专作民族研究工作的,实在不该有如此之担忧。壮族的构成成分应当有二:土著居民;外来移民后裔。这两支族人相互融合的结果形成今日的壮族。就算外来移民后裔都挂回原籍,也还有土著居民无处可挂,这不是“依据”吗?《考辩》者可能是不会挂的,不是还有依据吗?挂也并非易事,你若是土著,你对中原了解吗?你能挂上哪一家的哪一支?土著居民如果也有家史记载或传说,至多也只能挂到“武陵蛮”。历史研究应当客观,不能掺入臆想。不能凭借“以其故俗治”这点统治方略,把所有的外来移民都断定为“内气”,把其余的可能统统抛之而不顾。其实有利用价值的土著都封了官,难道有能力的外来移民就不得封官?得封官就是土著?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元素,通过婚姻的纽带,可以结成网,外来的同样有提携之人,怎么又当不了官?按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择官的重点应当是中原移民,而不是土著,用土著实不得已。《考辩》者在《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》中说:“也正因为元朝最高统治者视少数民族为‘吾民’,自然将其土官视作‘吾官’,等同于流官,于是出现了流官领土官,土官也领属流官的现象。”文中还说:“… 元世祖即同意湖广行省关于广西左右江太平、田州、来安、镇安四路总管府因‘所调官畏惮瘴疠,多不敢赴,请以汉人为达鲁花赤,军官为民职,杂土人用之’的奏请,以汉人为达鲁花赤。”这些话说明,制度与治情并不完全吻合,其外往往有很多细节存在,罗黄貌能在地州立足,自有其不为史载之原因,凭着主观置疑就认定其为土人,是有失偏颇的。历史是复杂的,研究不到家,不宜急于作结论,不能采取省力的捷径,通过否定几家官谱,就可以为壮族增添了几个姓氏,这样一来,渊源有自的独立民族群体-壮族就可以拥众自居。说实话,土著壮族为数应是有限的,从过去他们不断迁徙、不断开发拓展、不断流动的情况判断,他们并未得到安居,不可能正常繁衍生息,生产力之低下,不可能有丰厚的物质成果。由于条件的限制,决定他们拥众不多。至于官族是不是土著,我没有参论的必要。但从现在的说法去看,分析得那么整齐划一,凡是官族都是土著,官族,这一事物,只有一面性,来源也是一言以断之:本地。这些说法靠的是分析,而不是实在的记载,分析是带有错或对两面性的。罗氏的谱传,颇顺源流,能断为假?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情况下,结论是不能服人的。前人的有些说法,到底说明什么,《考辩》者根本不去很好想一想,就下论断。比如引了柳宗元所咏的“青箬裹盐归峒客,绿荷包饭趁墟人。鹅毛御腊缝山罽,鸡骨拜年占水神。愁向公庭问重译,欲投章甫作文身”之后,诘问“指的是什么人?”这样的问题,柳宗元能帮《考辩》者什么忙?柳宗元描述的自然是不同于汉俗的广西壮民俗,是肯定壮俗的存在。这一点谁会有疑问?但柳宗元并非特指官族姓氏。是《考辩》者要作连线的。这种理解与众人大相迥异。柳说的自然是他看到的或听说的当地人,头两句所说的情况,是没有塑料袋、没有饭盒、而只有竹筒而又忘带或不带竹筒时代的情况,不管什么人,处在这样的情况下,都会这么做。这不是壮族的特点,是环境、条件使然。更不是几家官族的首创。这是广西这一地域居民生活经验积累最终形成的生活习惯。这些当地人主要是壮族,但谁又能排除移民的入乡随俗?谁说入乡随俗了就是土著?《考辩》前言还罗列出前人的诗句:“夷俗不知文化近”,“细嚼槟榔血点唇”,“花布抹头是壮老”,“何时弓箭暂离身”,“饮食行藏总异人”,“衣襟刺绣作文身”,“男女分行戏打球”,“情歌互答自成亲”。《考辩》者接着诘问:“又是谁家的文化?”《考辩》想说明什么问题?这些壮族的习俗,自然是壮族的文化,只能套在壮族的身上。这些诗句又怎能说明官族就是壮族?外来的移民处在壮族习俗的包围中,他们也会从流的,比如着装,他不可能不用壮家的布,难道他们会回原籍去买布缝衣不行?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。上述诗句能说明什么?汉族出国,西装革履,你能说他不是汉族?壮族出国,西装着身,你又能说他不是壮族?还有没有提到的三响一扣宽头裤,壮、汉同装君可知?穿着宽头裤,是壮还是汉?《考辩》者引个别的说法,认定“十罗九古皆壮村也”。其实罗人很早就已进入广西(见下文),个别人的推断一定是正确的?罗村名罗,可能也是“攀附”中原了?湖北有罗田地名,能说那里的罗人也是土著?《考辩》试图以柳宗元“异服殊音不可亲”(《柳州峒氓》)的诗句说明官族都是土著,是不可亲的壮族。操壮语肯定有异音,着俗服肯定有异样。“不可亲”于个别群体是可说的,如当作普遍性,移民又能到哪里去结亲?又要回原籍吗?广西壮族纯朴敦厚,善于融合,乐于融合,尊重外来,恩思投报,迄今亦然。这是普遍性。有些分析者否定外来论,坚持土著论,只搞一点论,从而否定民族融合的存在。如果融合现象不存在,现在的壮族不大可能有几千万人的规模。历史是以事实构成的,不要把事实的历史变成分析的历史。
《考辩》的前言部分说:“传闻明初傣族人没有姓氏,其首领请官府给定个姓”,“操壮傣语支各族,其姓氏都是后具的”。虽说是“传闻”,可以信其有。因为少数民族文化确实不同于汉族文化。以此传闻推及壮族也无不可。但不能因此而随意寻求对象来套上。由上面的传闻而得所有的官族姓氏包括罗姓都是后具的结论,谁会相信?人们会问:罗氏官族前具什么姓或名,后才具什么姓或名,是哪个官府定的?其实各家都有“香炉不断千年火”,自家源自自家知。《考辩》的逻辑推理如下:“传闻”傣族原无姓氏→因此壮族原来也无姓氏→操壮傣语支各族原来均无姓氏→土官是壮族,因此也原无姓氏,现在他们所用的姓氏都是后具的,是攀附中原的。多么理想的立论,多么稳当的依据,土官是土著,多么吻合的结论!但却有与《考辩》料想不到的事情。罗人自秦汉时起,已有迁移之动态,有一支罗人已进入广西地区,这些早期移民的历史,岂能抹杀?说罗世念、罗黄貌是土著的说法,在广西从来没有如是之说,广西僚人家园点出的壮族姓氏中,也没有点到罗姓,只有个别人,持此异端。区外有载汉代郭公之子逢公徙广西天河县;汉末建安时辇公之子令帛、令希二公徙广西太平府崇善县;汉元和时生的季章公三子德公后徙广西宜山县黄家村、天河县袁村等处;臣恭公长子汉元康丙辰年生的诚公(第五世),五十八岁出任广西谏议大夫;汉元康己未年生的崇公十世孙季萱、季万公徙广西太平府崇善县,支分庆远、宜山、天河等处;汉王莽篡位间芗公徙广西罗阳县;晋章公,晋建元甲辰年生,大元间,徙广西南宁府隆安县,后分武鸣、来宾、宜武等处。这些材料证明广西并不是壮族一统天下;证明《考辩》者之“由于自然的‘烟瘴’和人为的‘以其故俗法(治?)’像两道护膜,将壮族社会包裹得紧紧的,外气入不去,内气出不来”的说法是臆想的; 还证明《考辩》者之“壮族居地,远离历代王朝的中心地区,人口稀少,岭树重遮,热气薰蒸,明时还是个大象出没之所,‘鳄鱼夜吼声如雷’之区,草长林密,雨水充沛,高温郁热,病疫流行,自古称为‘瘴乡’。中原人谈‘瘴’色变,闻‘蛮’气馁”说法,是夸大其词的。即使个别人或少数人暂时不习惯,觉得不适,也不能说明中原不敢移民。再说,《考辩》所说的罗氏官族是生活在与贵州临界的地方那地州,天气凉爽,四季分明,风景独秀,比江西还好住,哪来的“中原人谈‘瘴’色变”?分明是抄袭堆砌形容词,自以为外界不了解,就可以任其述说,别人不了解,桂西人了解,桂西人生于桂西,长于桂西,比《考辩》者更有发言权。前几年,中国科学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研究员在河池某地作报告,报告称广西及贵州是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。这与《考辩》者的说法,形成鲜明的对照。从秦、汉时代到现在,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短的区间,气候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。要说有区别,那就是开发程度较低的问题。但岭树重遮有什么不好?正好可以调节气候。《考辩》者想,把广西说得越过头越好,试图说明江西罗人无法进入桂西,在桂西的罗人(罗世念支系),是土著,姓罗是后具的,是造假。从立论到论证,都经过一番的苦心设计。从各支系的家谱看,历朝历代都有罗人迁入广西,广西成了罗姓大省之一。家谱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,正史有很多材料是缺遗的。历史就是历史,历史哪能因有人另有看法而改变?“传闻”既可以用来论证土著的立论,同样传说也可以证明支系的脉流,怎能变成了“造假”?《考辩》者煞费苦心,总难自圆其说。《考辩》者总提之时,是否定罗氏在广西的存在的,但在分说之时却又不敢否定罗姓,用“后具”二字作补,论据却无法服人。支吾持假,哪能有什么有力的证据?
历史有记载:“秦徙中县之民。使与百粤杂处”、 “我国东晋到明朝初年间,原来住在中原一带的居民三次向我国南方的大迁徙”。被动移民、主动移民的现象,历史上都存在。早期移民融入广西已有说明,不容置疑,融入何种民族当视情况而定。移民虽然融入异族,但他们毕竟有自己的根。根之存在是客观的。秦、汉已有罗人移民广西,后于宋、元入桂就没有可能?死咬那地州罗姓就是土著,但对那地州罗姓的来历却又无法考究,破绽百出,这是什么学术?
《考辩》之前言部分说:“今日壮族最主要的文化特征是操说自己的民族语言”。又想在特征上做文章。这种论断虽然没错,但并不全面,只对一半。融入壮族的移民,因受语言环境的影响,逐渐改变原来的语言而操当地的语言,甚至可以变成壮语语言的传人。这种事历史上不乏其例,如回族,还有几人能说阿拉伯语?满族,还有几人能说满族语?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少数民族的存在。同样,说壮话的也不一定都是千古不变的壮族。生活需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,所操的语言与民族并不能完全划等号。本人就看到一位随父母下放的北方青年,因收税工作的需要,与当地人打成一片,三个多月即可说出一口流利的壮语。此例足可说明,任何人到了广西,只要需要,只要用心学,都可以学会壮语,操壮语并不一定是壮族。话又说回来,早期移民的后裔,不仅改变原来的语言操说壮语,加上婚姻的关系,随母系自然而然变成壮民族的成员,随父系他们依然还有自己的根可寻。广西的真实情况应当如此。如果这样认识,倒还接近事理。要说壮族的语言文化特征除了操说壮语之外,绝大部分壮族都能说流利的汉话(普通话、大西南语言圈的汉话、少数知晓白话)是个多语民族,我看这也是特征,也是移民后裔语言文化上善于融合的特征。提出壮族的文化特征,能证明那地州罗人就是土著?
《后汉书》有载:“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,帝患其侵暴,而征伐不克。乃访募天下,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,购(赐?)黄金千镒,邑万家,又妻以少女。时帝有畜狗,其毛五采,名曰槃瓠。下令之后,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,群臣怪而诊之,乃吴将军首也。帝大喜,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,又无封爵之道,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。女闻之,以为帝皇下令,不可违信,因请行。帝不得已,乃以女配槃瓠。槃瓠得女,负而走入南山,止石室中。所处险绝,人迹不至。于是女解去衣裳,为仆鉴之结,着独力之衣。帝悲思之,遣使寻求,辄遇风雨震晦,使者不得进。经三年,生子一十二人,六男六女。槃瓠死后,因自相夫妻。织绩木皮,染以草实,好五色衣服。制裁皆有尾形。其母后归,以状白帝,于是使迎致诸子。衣裳班兰,语言侏离,好入山壑,不乐平旷。帝顺其意,赐以名山广泽。其后滋蔓,号曰蛮夷。外痴内黠,安土重旧。以先父有功,母帝之女,田作贾贩,无关梁符传、租税之赋。有邑君长,皆赐印绶,冠用獭皮。名渠帅曰精夫,相呼为B769徒。今长沙武陵蛮是也。”(摘自国学网)
这是传说,不足为据,但其中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。我们可以想像,从武陵到岭南,由岭南而至岭西(即岭表西端)古代越人由东向西迁徙,逐步进入桂西,这是由他们“好入山壑,不乐平旷”的特点决定的。原因不外是躲避战争或开拓的需要。说是桂西,但这些先民的分布情况并不很清楚。桂西开发较晚,人烟稀少,移民尽可开发。并不像《考辩》前言所说的。至于说什么“壮族居地,远离历代王朝的中心地区,人口稀少,岭树重遮,热气薰蒸,明时还是个大象出没之所,‘鳄鱼夜吼声如雷’之区,草长林密,雨水充沛,高温郁热,病疫流行,自古称为‘瘴乡’。中原人谈‘瘴’色变,闻‘蛮’气馁”。这种说法是想要人们相信,中原人绝对来不了广西,从而否定移民的存在,在广西生活的都是“土人”,为其立论服务。据文载,罗人翻山入川、入滇、入黔,甚至向中南半岛迁徙,也有进入朝鲜半岛谋生,还有飘洋过海,进入东南亚建立兰芳共和,比广西艰难的地方都不能阻挡罗人的步伐,难道就进不了与湖南接壤的广西?难道就进不了“千山拥洞,岭树重遮”一片阴凉的那地?
在广西,谁都知道,壮族有两种构成成分:一为越人后裔,即土著壮族;二为移民后裔,融入的壮族。这两支族人构成当今的壮族。由于相互融合,现在已经分不出谁是原住土民,至于融入者则各有自己的家传。而壮话则为大家共传承。
《考辩》前言说:“如果遵从明、清土官们的说法,今日各姓氏壮族人的声言,他们操说的壮语从何而来?”像这样的问题,能说明什么? 这不就是融合带来的结果吗?人去的确楼空,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,传承自会不绝。不因为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缺位而不存在,旧的传人走了,新的传人承接,只要生活生产需要,它永远不会失传。移民由于需要,就得入乡随俗,操起环境需要的语言,语言无优劣之分,语言为交际所需要,适用就好。移民不一定都留恋母语的富丽,环境变了,他们也会跟着变,只要生存需要,什么都得服从这一需要。韧是移民的特点,善变也是移民的特点。移民因说另一种语言就不是移民,就是土著,这种结论令人难以恭维。按照《考辩》之说,过去的广西全是土著人居住,说是移民,不是;原为移民,也不是。广西有个土著的加工厂,难怪广西有不同于其他省的民研结论。作为学术研究,随你怎么说,有没有人相信也用不着去管。学术应当自由。但把不成熟的研究,到处传销,阻碍别人修续家谱,实在是过分,这就是逼人回应的原因。历史的研究对与错,不是一人说了算,以一己之结论强加于人,十分少见。如果是真理,又何忧不为人所接受?万马齐喑的时代已经过去,莫非又想拉回来不成?
2. 《考辩》前言引明人刘昌《悬笋琐探 .膺谱》(载略),此为个例。
又引清人王崇简《谈助 .连谱恶习》“凡舆抬皂隶,苟家业千金者,无不与遥遥华胄共相附丽”,“更若远方来宦,一值同姓,鲜不同宗,以致东西南北之人水木本源千里神合”。此种情况会有,至少在王崇简的周边存在,要不然他怎会说出这样的话?但引用者却无限地夸大,把这当作立论的基础、土论的救命。攀华附贵作为一种现象,每个朝代都有,不可否认,但是不是所有的家谱都是如此?如果如此,那贵胄有传,贫民无后了,除了贵胄家谱可信(因无需攀附),其余家谱都不可信了。据我所见,诸多家谱只重脉流,不从职级,是则是,非则非。非常客观。如果把特殊的事例当作一般,而把一般当作特殊看待,还有什么是可信的?如此一来,华胄之外的族谱都是白修了。
“明、清以后,无论省志、县志,还是私家所撰的谱系,莫不声言土官们的先人是中原来人,源于中原的著姓望族,因随狄青南征侬智高立功授职方才落籍于桂西的。现在,此风仍频吹不止,大有越吹越劲之势。1998年出版的《壮族通史》肯定了此种说法”,这是《考辩》的唯我独尊的说法。试想,浩浩荡荡的几万大军南征剿侬,能不留下一兵一卒以戍边?一提到此事,便是攀附中原?考无凭依,议而有论,这是研究吗?《考辩》还说:“壮族土官诸族谱追源溯流,夤缘攀附于中原名姓望族”。《考辩》的前题是自己创造的,先把官族说成土著,于是便来任意发挥。不信,请看原文,官族的先世从何而来,说得清楚吗?愿说清楚吗?既不清楚,又从何得来的结论?《罗氏宗谱》中,始祖说对了,后世的世次很连惯,中间有错漏,这是实在的,但却一字不提,尽量回避,对于那些以后世之语述先世之爵的毛病却大加挞伐,有失公正。其实,谱载累累有误,这是常事,是诸多原因造成的。正如《考辩》之原书《壮族土官族谱集成》错字之多令人惊讶,何必又来五十步笑百步?广西的土著就那么了得,坐在偏僻的地广人稀的山旮旯,就能“胡诌”中原的世谱,广西的土官又那么愚钝攀附中原却不攀附赵刘朱王李这些名门贵胄,却偏偏攀附无帝王世袭的罗门,如此“攀附”也是攀附?先世的史载,不能说一切都正确,因惰于穷究,把不清楚的问题均归为“土”,这的确省了好多的麻烦,因为不需多少证据。此风现在吹得何等强劲!
“《罗氏宗谱》的编者为了说明那地州的土官罗氏始于明初“从江西南昌府分居那地州”的罗黄貌,编了一串“江西南昌府”从汉惠帝至明初罗黄貌的罗家世系,但他们忘记了明军进入广西,罗黄貌是作为元朝的“世袭土官归附”的,而不是罗黄貌作为明军将领进入广西因“征讨那地州猫蛮”有功而封于那地的。“反客为主”,固然可以变被动为主动,但“归附”明朝的客体那地州世袭土官罗黄貌,是不能变为“征讨那地州猫蛮”立功的主体‘明军将领’罗黄貌的”, “罗黄貌以前的所谓“江西南昌府”罗家世系是伪造的”。这是《考辩》的说法。
我没有必要为罗黄貌辩护,我不是罗黄貌直传。我只是旁支。如果罗黄貌造假,我也得不到什么荣耀。如确为造假,我也不会认可。是土著又有什么不可?但按世次推算,罗黄貌,那地州知州,任职居那地。约生于南宋景定年间至元朝中期以前这一段时间的某个时候。入桂当在元朝年间。官谱认为罗黄貌明初入桂实在有误,但作为元官归附明朝,客体归附主体,后朝视前朝官员、后政视前政官员为客体,这是自然的事。这那能成为“土人”的证据?又何以成为‘罗家世系是伪造’的证据?有误与伪造并不是一回事。结论下得太离奇。“那地土官罗腾皋说“我祖宗自宋讨平那地,仰沐累朝圣恩,念伟积丰功,奄有兹土,俾子孙世袭抚治之”。这指的是宋朝的罗世念,符合历史。但因罗腾皋所处的时代其地已称那地,故用那地之地名,只能说思维不慎密,造成错误,与家谱的真伪又有多大的关系?至于说到罗黄貌伪造家谱一事,《考辩》的理由也是牵强附会的。罗黄貌是武进士,已有封爵,其后世袭无忧,他有何必要去忧虑其后的世袭问题而去造假?既然他有为当时王朝出力的事迹,王朝岂有置之于不顾之理?土人立功尚且授爵,黄貌立功岂无官封?以家世考虑封官,罗黄貌后人已具条件,造假实在无必要。《考辩》说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。
《考辩》的论证有个特点,把常见的错误当作造假的证据,因立论是一个“假”字,故一切错误都是“假”的证据。真是欲加之假,何患无词。《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》中举了播州的例子,“…元末明初,播州土官宣慰使为杨铿,宣慰使土官同知为罗琛,播州总管为何婴,播州蛮夷总管为郑瑚,虽然罗、何、郑三姓土官都受辖于播州宣慰使杨铿,但是包括杨铿在内,他们四人各有治区,互不涵盖,各自传承,怎么能够因为播州宣慰司设有达鲁花赤,就否定了杨、罗、何、郑四人各自世代传袭的领地,否定土司的存在呢?”又是一个罗同知土官,可能又是姓“土”了。
《考辩》原书称《壮族土官族谱集成》,书中载明:第二部分族谱的收集及第三部分由谷口房男撰写。书后亦表示,“囿于闻知,失于周正,尚祈斧正”。不知是真心实意,还是客套。反正我觉得此书以专题研究为主,这点无可非议。但研究的内容却是壮族的内容。以小小的专题掩盖壮族的繁衍的历史流程,使人误解,广西壮族就是这几家,使人没有对比思考判断的余地。虽是专题研究,对壮族的大略情况也应书上几笔,无对比怎能分辨是非?全书说的尽是只一无二之话。让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的人信以为真。
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民族史有他的目的(其实他的研究能力是极为有限的,怎能捧为大旗?),如能把中原四周的民族与中原的联系统统割断,他才感到痛快。他的话能以为据吗?广西《壮族研究概述》有如是之说 :“第一阶段: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,外国人研究壮族。西方学者研究壮族问题始于19世纪末叶,其时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侵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,他们出于侵略的目的,需要了解这个地区的地理、历史、民族、语言、习俗等等问题,适应帝国主义利益需要,有些殖民机构的官员,有些传教的牧师,有些学者,先后进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作调查研究。最早是英国人(1880年,阿·柯奎翁;1909年,亨·理·戴维斯),然后是法国人(1897年,皮·勤·邦德里),美国人(威·克·杜德),他们从对缅甸的掸族、泰国的泰族研究起,联系到中国的壮族、布依族,他们通过对泰国泰族及广西、广东、云南文山壮族的实地调查,发现泰语与壮语的词汇基本或大部分相同,应该肯定这是他们调查研究的成绩。但遗憾的是,他们据此竟把壮族与泰国的泰族混同,并武断地说壮族就是泰族,把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都称之为泰族;西方学者的这种泛泰观点曾影响了泰国、日本学者,有些学者曾发表文章,把居住在中国的壮侗语族诸民族称为东泰,居住泰国的泰族称为西泰。”
我们修谱、续谱,并不是要改变民族,并不是要脱离广西回到中原,而是要弄清源流,尊祖敬宗,不做糊涂人。这与“壮族作为一个渊源有自的独立民族群体”有没有“存在的依据”又有何相干?壮族的存在是客观的,总会有“攀”不到中原家族世系的人,比如《考辩》者。而这些人应当作为重点研究而却只字不提,这是历史研究的悲哀。
《考辩》立论来势很大,但却论证无力,论据脆弱,原因是以主观分析为主,缺乏事实支持。
 查看更多
查看更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