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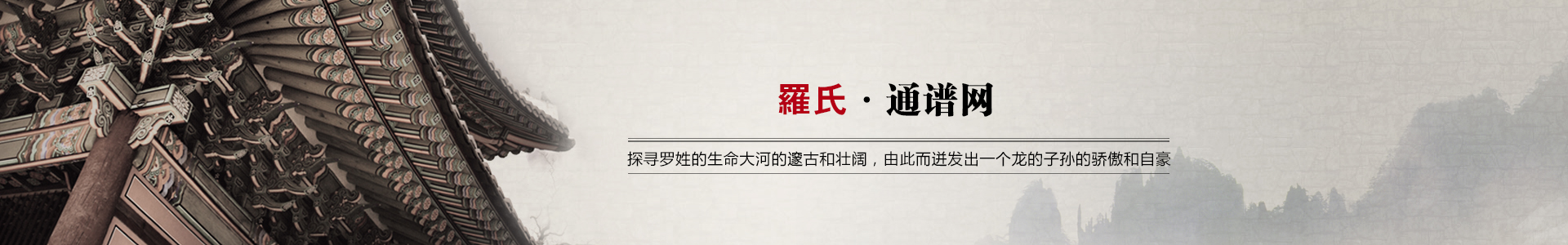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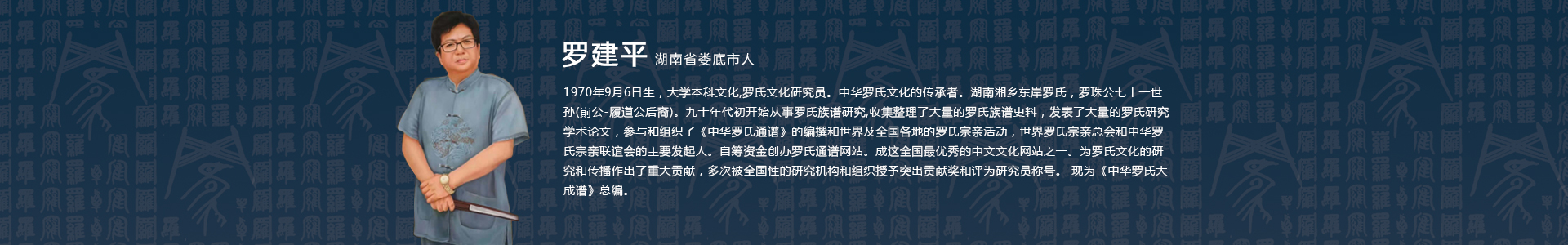
罗大经的诗学
施芳雅 发布时间:2005-05-21
一、 前 言
罗大经为南宋庐陵(今江西吉安)人。理宗宝庆二年(1226年)进士。所着《鹤林玉露》一书分甲乙丙三编,共计十八卷,其着书缘起,据自序云:
间居无营,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,或欣然会心,或 免兴怀,辄令童子笔之, 久而成编,因曰《鹤林玉露》。盖「清谈玉露蕃」杜少陵之句云尔。
《宋史.艺文志》着录于子部小说家类,《四库全书》收于子部杂家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其「体例在诗话、语录之间」,而是书半数以上评述前代及宋代诗文,以及记述宋代文人轶事、论诗主张,内容丰富,亦颇有见地。例如其在(卷三)论苏轼文章深受《庄子》、《战国策》影响,为后人誉为深具眼力之论。《鹤林玉露》一书中属于诗话部份总计有一百八十三则,近人孙肃编纂辑录成《罗大经诗话》,对研究南宋诗话,具重要参考价值。尤以乙编卷四「诗祸」一则,记宋理宗宝庆、绍定间江湖诗案一事[1],有助于对江湖诗派的了解,具文学史料价值。
兹就是编,批览玩索,其论诗主张,有当世理学家言志派诗论的风教传统兼江西诗派重视诗法的艺术性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罗大经「其人本文章之士,而兼慕道学之名」,此当是其论诗主张的渊源。他在论诗功能、创作技巧、审美鉴赏方面,自有其定见。此文拟将其诗学以功能论、技巧论、鉴赏论分别概述。
二、 功能论
从《鹤林玉露》一书,约略可窥见罗大经的交友与论学、生活与思想,其对人物的品题,论士大夫去就,持论甚严,而其个人亦颇能厉操守、处平淡;明代黄贞升在本书的「重梓题辞」誉其为「博雅君子」如「鹤舞云中」;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其着书「要其大旨,固不谬于圣贤也。」 但他身处南宋国势危累的时代,自不免有忧国之思,这勿乃是他强调诗之必须具有「劝戒之意」,达其社会功能与价值的最大外在因素。书中他在论事之余,亦往往依所论之诗,兴感应作。如:
柳耆卿作(望海潮),此词流播,金主亮闻歌,欣然以有慕于「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」,遂起投鞭渡江之志。近时谢处厚诗云:「谁把杭州曲子讴,荷花十里桂三秋。那知草木无情物,牵动长江万里愁。」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,卒为金主送死之媒,未足恨也。至于荷艳桂香,妆点湖山之清丽,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,遂忘中原,是则深可恨耳!因和其诗云:「杀胡快剑是清讴,牛渚依然一片秋。却恨荷花留玉辇,竟忘 因柳汴宫愁。」(一则)
他这种对士大夫承担家国兴亡的责任感有着深沉的期待,自然影响他在诗学上的见解,而趋向言志一派,因此他说,诗要能「微而显,得风人之体。」还要能承继三百篇「怨刺上政」的风教。如他分析杜甫(冬狩行):
自古夷狄交侵,中国衰微,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诚,将帅真有愤切之志,然后可以言恢复。杜陵(冬狩行)曰:「草间狐兔尽何益,天子不在咸阳宫。」规警将帅也。又曰:「朝庭虽无幽王祸,得不哀痛尘再蒙。」规警人主也。然人主者本也,人主果有兴衰拨乱之志,其谁敢不从?故又曰:「呜呼!得不哀痛尘再蒙。」所以深规警人主也。(三十六则)
这段文字,不仅敏锐的解读了杜甫的诗意,也「意在言外」地传达了他对所处时代之困局的深刻寄意。其次,根植于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,尤其自范仲淹倡「先天下忧」,影响宋朝知识分子崇尚气节之风所及,罗大经在论诗人诗坛地位和诗家人格的品评上,自是以具忧国忧民情怀的杜甫为高:
李太白当王室多难,海宇横溃之日,作为歌诗,不过豪侠使气,狂醉于花月之间耳。社稷苍生,曾不系其心膂,其视少陵之忧国忧民,岂可同年语哉?(五十一则)
对于李白诗在内容上脱离现实,不以系念苍生的诗歌创作取向,自北宋以来已多所批判,如苏辙就认为他「华而不实,不知义理之所在」,而所谓义理,也就是对天下百姓的承担。他曾举一例:
汉高祖归丰沛,作歌曰:「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」 白反之,但歌「大风云飞扬,安用猛士守四方?」其不视理
如此。(《诗人玉屑》卷十四)
是则诗除了要能言志,更要能「借物明道」,若一意在格律的精粗、用意、属对、比事、遣词的好坏上计较,实在看不出有什幺高明,与其同时江湖诗派作家之人品最为人所诟病,士行堕落,藉诗文为乞援之媒介,丑态毕露。钱谦益(王德操诗集序)云:
彼其尘容俗状,填塞于肠胃,而发生于语言文字之间,欲其为清新高雅之诗,如鹤鸣而鸾啸也,其可几乎?(李曰刚《中国文学流变史)
所谓「诗者志之所之,岂有工拙哉?亦观其志之高下如何耳。」(一七七则)他在诗话中时引朱熹的意见为意见:
近世作者,留情于此,故诗有工拙之论,葩藻之辞胜,言志之功隐矣! …. 无复古人之风矣!(一 七七则)
并且极推崇朱熹,他举其诗为例,认为胸次高、方寸意态不着一俗字,那幺诗不期高远而自高远:
公尝举其所作绝句,示学者云:「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」 盖借物以明道也。(一七七则)
又引杜甫诗:
杜陵诗云:「新松恨不长千尺,恶竹应须斩万竿。」言君子之孤难扶直,小人之多难驱除。呜呼!世道至于如此,亦可哀矣!(一六则)
「道」的意涵有宇宙之道与人世之道之不同层次,然「诗以载道」的思想为其
诗论所再三强调。诗若不能达到诗教的正面意义与价值,则创作亦是枉然,他说:
古诗多矣!夫子独取三百篇,存劝戒也。吾辈所作诗,亦须有劝戒之意,庶几不为徒作。(二四则)
他并以独到且慎警的角度批判白居易的诗,他认为部份白诗有颓废意识,对社
会风气有负面影响:
白乐天(对酒)诗曰:「蜗牛角上争何事,石火光中寄此身。随富随贫且欢喜,不开口笑是痴人。」又曰:「百岁无多时壮健,一春能几日清明。相逢且莫推辞醉,听唱阳关第四声。」又曰:「昨日低眉问疾来,今朝收泪吊人回。眼前见例君看取,且遣琵琶送一杯。」自诗家言之,可谓流丽旷达,词旨俱美矣!然读之者必将起其颓堕废放之意,而汲汲于此快乐惜流光,则人之职分,与夫古之所谓三不朽者,将何时而可为哉?…. 慕乐天者,爱而知其疵可也。(二四则)
由此可知罗大经在诗学中的思想论是以淳谨雅正为宗,所以进而提倡「温柔敦厚」的诗风,亦即诗之词意要委婉,要「优柔谆切,怨而不怒。」(七十二则)他举李白诗(去妇词)与诗经(谷风)去妇词相较,认为诗人传达情感不宜太「豪便」露骨,要不偏不激、不迫不露。这一观点与较他稍早的杨诚斋相一致,诚斋在其《岁寒堂诗话》言白居易长恨歌「汉皇重色思倾国」,浅露、「无礼之甚」。罗大经对诚斋颇扬誉,二人论诗率尚「忠厚」之风:
李太白(去妇词)云:「忆昔出嫁君,小姑才倚床。今日妾辞君,小姑如妾长。回头语小姑,莫嫁如兄夫。」古今以为绝唱,然以余观之,特忿恨决绝之词耳。岂若《谷风》去妇之词曰:「毋逝我梁,毋发我芶」虽遭放弃,而犹反顾其家恋恋不忍乎!乃知《国风》忧柔忠厚,信非后世诗人所能仿佛也。(七十二则)
综上所述,罗大经在诗学上的观点,承继儒家传统的诗歌功能之价值论,殆无疑异,是故延伸到诗的创作方法上也必然「重比兴」、「贵含蓄」,以下则针对其创作理论之根源与创作技巧稍加论略。
三、 技巧论
罗大经的诗歌创作理论有其特殊的学术思想背景,大概都受到朱陆理学的影响。他认为具体的知识要透过「读书」去探求,但也要能「虚心观理」「先求我心」,他将两者巧妙应用在诗学创作的基础上。譬如他说:
余谓渊明性质高迈,其言曰:「得知千载外,上赖古人书。」又曰:「羲农去我欠,举世少复真。汲汲鲁中叟,弥缝使其淳。」则其于六经孔孟之书,故以探其微矣! (一三一则)
此言读书与真淳并不相悖,而陶渊明诗之成就亦端在此二者。又说:
北魏主珪,问博士李先曰:「天下何勿最益人神智?」先曰:「莫若书。」王荆公诗曰:「物变有万殊,心思才一曲。」读书谓耶!夫着一能读书之心,横于胸中,则锢滞有我,其心已与古人天渊悬隔矣!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?若锢于有我之私,不能虚心观理, 是乃不能读书也。(一六七则)
这主张与杜甫「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」的积蓄功夫有相通之处。除读书一端,还得虚心观理,才能进行艺术创作,刘勰《文心雕龙。神思篇》曰:「是以陶钧文思,贵在虚静。」罗大经对这点也有所阐述:
每于活处看古人观理,,故诗曰:「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」,夫子曰:「逝者如斯,不舍昼夜。」又曰:「山梁雌雉,时哉!时哉!」…..又养小鱼,欲观其自得,皆是于活处看。
因此他说魏鹤山(读易亭)之咏梅诗「推究精微」无人能及,(一七六则)盖其意为:诗人若能掌握自然中的理趣,则自能写物,而道亦在其中矣!而写物、喻道,要能「含蓄不露」浅俗、直陈之诗,「无味」且「乏蕴藉」不能称为好诗。举李商隐为例:
唐李商隐(汉宫)诗云:「青雀西飞竟未回,君王犹在集灵台。侍臣最有相如渴,不赐金茎露一杯。」讥武帝求仙也 。…..二十八字之间委蛇曲折,含不尽之意。(五七则)
而欲求诗情的「含蓄」,非藉「比兴」不为功,其云:
诗莫尚乎兴,圣人言语亦有专是兴者。~盖兴者因物感触,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,义味乃可识,非若赋比之直言其事也。故兴多兼比、赋,比赋不兼兴,古诗皆然。(一O四则)
诗作之中若「兴中有比」,则意味更深长,他举以下名家佳句为例:
诗家有以山喻愁者,杜少陵云:「忧端如山来,项洞不可掇。」赵碬云:「夕阳楼上山重迭,未抵春愁一倍多。」是也。有以水喻愁者,李颀云:「请量东海水,看取深浅愁。」李后主云:「问君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」秦少游云:「落红万点愁如海。」是也。贺方回云:「试问闲愁都几许,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。」盖以三者比愁之多也,尤为新奇,兼兴中有比,意味更长。(六一则)
大体而言,在创作的表现方法上,罗大经的立论不脱前人窠臼。但在艺术技巧上却有些见解的。他认为诗家作诗要善于用字,有所谓「健字」、「活字」、「助字」、「迭字」的讲究。他说:
作诗要健字撑拄,要活字斡旋。如「纪入桃花嫩,青归柳叶新。」「弟子贫原宪,诸生老伏虔。」入与归字、贫与老字,乃撑拄也;「生理何颜面,忧端且岁时。」「名岂文章着,官应老病休。」何与且字、岂与应字,乃斡旋也。撑拄如屋之有柱,斡旋如车之有轴。文亦然,诗以字,文以句。(一七五则)
诗用助语字,贵妥贴 。(七六则)
所谓「助语字」即是虚辞,如杜甫「古人称逝矣,吾道卜终焉。」,「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。」用得浑然妥贴,毫不损于诗歌的简炼之美。而创作的态度要敬谨,主张「作诗必以巧进,以拙成。」也不必速求于一时。其曰:
作诗必以巧进,以拙成。故作字惟拙笔最难,作诗惟拙句最难,至于拙, 则浑然天全,工巧不足言矣! 杜陵云:「用拙存吾道。」夫拙之所在,道之所存也。(二十五则)
子美寄太白云:「何时一樽酒,重与细论文。」「细」之一辞讥其欠缜密也。 余谓文章要在理意深长,辞语明粹,足以传世觉后。岂夸多闻速于一时哉 ?(一七一则)
以上是罗大经对诗歌创作见解,内容与形式并重,无论是大原则或文词的小技巧都面面具以论之。这使得他在鉴赏诗歌有异于他人的慧眼和独特的看法。以下略述其概。
四、 鉴赏论
罗大经在诗歌的审美上有向往或回归古典意趣的倾向。崇尚自然简远,真澹箫散的诗风,而这也可从他的生活得到印证。他有一段佳文,述及山居生活,惬意从容,读书、品茗与自然共俯仰,云:
山之中,每春余家深夏之交,苍藓迎阶,落花满径,门无剥啄,松影参差,禽声上下,午睡初足,旋汲山泉、拾松枝、煮苦茗啜之。随意读周易、国风、左氏传、离骚、太史公书、及陶、杜诗,韩、苏文数篇。从容步山径、抚松竹,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。坐弄泉流、漱齿濯足,既归竹窗下,则山妻稚子,作笋厥、供麦饭,欣然一饱。弄笔窗间,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贴笔迹画卷纵观之,兴到则吟小诗,或草《玉露》一两段。(二九则)
由此段描述可以知其人之风格品味。而他雅好杜诗、善解杜诗,由以下一则文字可以看出其鉴赏力之深厚:
杜少陵诗云:「万里悲秋长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。」盖万里,地之远也;秋,时之惨凄也;作客,羁旅也;常作客,久旅也;百年,齿暮也;多病,衰疾也;独登台,无亲朋也;十四字之间含八意,而对偶又精确。(一二四则)
如何可以具高度诗歌鉴赏力?他要求欣赏者必须选取一定的角度,并具有一定的修养,所谓「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」之说。其曰:
杜少陵绝句云:「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。泥融飞燕子,沙睡暖鸳鸯。」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异?余曰不然,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,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。于此而涵泳之、体认之,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?
大抵古人好诗,在人如何看,在人把做甚幺用?如「水流心不竞,云在意俱远。」,「野色更无山隔断,天光直与水乡通。」,「乐意相关禽对语,生香不断树交花。」等句,只把作景物看,亦可把作道理看,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。大抵看诗,要胸次玲珑活络。(七九则)
以上为罗大经提出个人在诗歌鉴赏上的体悟,好的诗作往往都是物中喻理,景中喻情,情景交融,使鉴赏者透过创作者的隐喻、暗示,产生移情作用,理解诗人的思想情感,达到和诗人一致的情境,而蓄发内在心灵的共鸣,使创作与审美有了高度的结合。作为一个读者若平日无所涵养蓄积,不能虚心观道,诚心体物,纵便有好诗,也无从品味,更不知佳妙何在,亦是枉然。
五、 结论
综观罗大经的诗学,其思想、创作、鉴赏都有其相当整次的思想脉络可寻,也深具一贯性,虽是随笔、短语、散论,经过阅读、扒梳、归纳未见有扞格抵牾,相与难容之论。其对各诗家风格的掌握,如说子美精工、乐天蕴藉、东波超迈、诚斋透脱等俱称允当,为治文学史家所乐为引述,是其在诗文的批评上固宜据一席之地。
 查看更多
查看更多
